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
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兴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这是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和运动都更广泛、更猛烈、更震动人心的思潮和运动。
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正是这个时期兴起的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兴起的,并且有着自己产生的社会的和阶级的根源,但它仍然与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受到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曾经有人说,中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支流。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它曾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某些影响,这则是历史上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应该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的,但在过去,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却是怠慢了的。
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如果从《播种人》的发刊算起,它有着十多年的战斗历史。它抗击了法西斯的暴政,进行过有声有色的斗争。它拥有庞大的理论队伍和创作队伍,产生了相当出色的作品。当时,国际作家联盟肯定过它的战绩。
中国是日本的近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人员的往来也很频繁。所以后起的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向日本的经验学习,受了日本的某些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1983年刘柏青老师与伊藤虎丸(左)、山田敬三(右)
提到这种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它归因于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的成员都是日本的留学生,特别是后期创造社成员,都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离开日本,归国倡导革命文学的。他们在日本感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热烈气氛,受到一些思想、理论的熏染,回国以后,自然要把日本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中去。这样看当然是正确的。但除了这样一条而外,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受了日本的影响之所以可能,还在于两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有着近似的某些历史条件。
首先,它们有着大体上相同的资产阶级文学传统。在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很短,十分软弱,这是不用说的了。日本的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开始的资产阶级文学,虽然比中国早了几十年,资格较老,但也是软弱的,发展的并不充畅。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旧的负担较轻,而资产阶级文学不能构成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严重威胁。而同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的口号之前,也都有一个准备的时期。
第二,两者也大致上有着相同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日本的情况和中国不同,但《二七年纲领》、《三二年纲领》都规定了日本的革命性质是以急遽的速度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阶级关系上对待资产阶级虽然和中国有所不同,但也有反封建的任务;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两国共同的战斗任务。
第三,两国反动政权的迫害是同样残酷的。
第四,都是以俄为师。
第五,都有党的错误路线的干扰。
最后,运动的基本力量都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方法。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些相同的条件,后起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理论上思想上,或多或少受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潮影响才成可能。
下面让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影响。
左联成立前后,一个很有意义并且很有成绩的工作,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但这项工作的规模和重点是很受了日本同样工作的影响的。因为,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不说百分之百,也是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转译的。所以日本这一工作的面貌,就决定了中国的同样工作的面貌。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日本主要翻译介绍了普列哈诺夫、弗里契、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波格达诺夫、德波林的东西,而少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他们与其说是通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勿宁说是通过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波格达诺夫等人的著作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他们文章中引用的据为经典的是普列哈诺夫等人的言论,而很少有马、恩、列、斯的。在中国,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沈端先虽然在一九三〇年就介绍了列宁的文艺观,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在一九三四年始见有人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的文章也是一九三四年才开始出现。一九三二年以前,一些理论文章中,也是大量地引用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达诺夫等人的论点,甚至是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的论点。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论著,如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人的文章,也曾被目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典范,大量地翻译过来。日本的辛岛骁说过:“日本左翼评论家的议论,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特别是平林初之辅、片上伸、冈泽秀虎、青野季吉、藏原惟人、川口浩等的文章,曾经和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并列,象金科玉律地被引用过。”看看当时的一些评论文章,觉得辛岛骁的这番话,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夸张。
一九三一年,在苏联,斯大林发表了《论布尔塞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这是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批评了对于布尔塞维主义(编者注: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反列宁的倾向,强调了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号召要把理论工作推向列宁的阶段。以这篇文章为导引,苏联的理论界、文艺界开展了一场较广泛的批评活动,集中地批评了普列哈诺夫、弗理契、德波林、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达诺夫等人的反列宁的文艺思想,当时的口号是把文艺理论推向列宁的阶段。这种动向,很快地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有了强烈的反映。一九三一年十月藏原惟人化名古川庄一郎,在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的刊物《纳普》上发表了题为《为艺术理论的列宁主义而斗争》的文章,所论问题的口径完全和苏联的批评活动相一致,不外是说,过去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受了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严重影响,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这些人的观念论、机械论的机会主义的艺术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统。更值得注意的是藏原惟人在这篇文章中号召人们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上,对于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指导理论的藏原惟人、中野重治、鹿地亘、川口浩等人的理论,进行彻底的清算,特别是要清算藏原惟人的理论,因为它最系统,影响也最大。
苏联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发生的新动向,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中国也有反映,刊物上陆续出现了批评普列哈诺夫、弗里契、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缓慢地发生了变化。
总之,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是和日本的情况联系着的。谈到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影响。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也显露了弱点,出现了错误。这个运动虽然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但它的酝酿和行进,受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一些影响,这一事实是不能不看到的。起初,究竟用什么词语来概括这一文学运动,大家是很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叫革命文学,有人叫新兴文学;普罗文学,第四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种种叫法都有。这情况很象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初期。
当时的革命作家,主张文学的阶级性,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翼,这在推动文学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这一点上,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样的文学,由谁来做呢?创造社和语丝派之间,曾经有过争论。包括鲁迅在内的语丝派的作家还有郁达夫,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做,现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开口,文学家都是读书人,所以现在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创造社的作家则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我们知道,在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初期,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当时反对者所持的论点仿佛也和语丝派或郁达夫一样。他们赞成无产阶级文学,只是不能同意知识分子搞的那种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有菊池宽和有岛武郎,有岛武郎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论文《宣言一篇》里。这篇东西鲁迅已经翻译过来,我们是熟知的。有岛武郎等人的意见也受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们的批评,像片上伸、士界利彦等人都写了文章,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在现阶段就得由具有无产阶级目的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做。日本的这场斗争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八年中国好象又把它重演了一次。但不一定说鲁迅等人受了有岛武郎的影响,因为在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可能出现相类似的事件的。但创造社作家从理论上说明知识分子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时,确乎是借鉴了日本的理论观点。
创造社的作家们认为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是可以而且必得由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做。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命题,一些人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展开,真正做了理论的阐述的是题为《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普罗文学,是一种目的意识的活动,如果它是一种表现的东西,那么表现出来的,结局是一些大众自然生长的意识,这谓之曰对于自然生长的屈服。”“我们中国现阶段的普罗文学,本来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意识战野这方面的一支分队,所以严密地说来,它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前卫)的一种意识的行动,而且能担任这种任务的,在现阶段,只有革命的知识阶级,所以,对于普罗作家的批评,只能依他的意识为问题,不能以他出身的阶级为标准。”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受了日本的某些理论家特别是青野季吉的影响的。青野季吉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曾发表了一篇给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以很大冲击的文章,它的题目就是《自然成长性与目的意识性》。这是把列宁的《怎么办》的第二章中所论述的理论观点机械地搬来用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上。青野认为,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学是自然成长的,只不过是无产阶级自发地表现自己,是个人的满足,必须把这种自然成长的文艺,提高到目的意识的文艺,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具有目的意识的艺术家把自然成长的无产阶级文艺,提高到目的意识的高度的文艺运动。后来林房雄又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说:无产者运动中的大众行动,是非意识的,自然成长的;前卫(先锋队)的行动是目的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是前卫的运动,也就是具有无产阶级目的意识的运动。
我们如果把中国的《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的论点和青野季吉等人的论点两相对照,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中国的《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的论点如果不是以青野季吉的理论为依据,也是受了青野季吉等人的影响或启发,这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到了一九二三年的九月由于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遭到挫折。一九二四年以后又重整旗鼓,进入了“第二斗争期”。这时理论主张深入了,而在理论上的代表人物就是青野季吉。他的《自然成长性与目的意识性》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要在文艺运动中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权,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但由于机械论的缺点,招致了刚刚成立一年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团体日本普罗文艺联盟的分裂。青野的论点,被概括为目的意识论,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的。这个目的意识论,对于中国的文艺界影响也很大。当时甚至把目的意识当成文艺批评的标准,把是否具有目的意识看成是区分无产阶级文艺与非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作家与非无产阶级作家的界限。在一些文章里原封不动地引用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这样的字句,甚至左联成立以后,在一篇谈左联成立的意义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不是自发性的社会运动的文学运动,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即没有目的意识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不会有的。”足见目的意识论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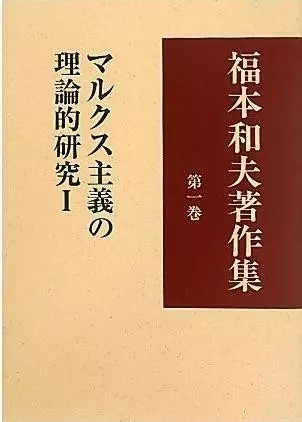
福本和夫(1894—1983)是日本共产党左倾的福本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图为《福本和夫著作集》(来源:网络)
抛开实践,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目的意识,机械地搬用列宁的教导,青野季吉未必是始作俑者。在他发表《自然成长性与目的意识性》这篇文章的一九二六年,正是福本主义在日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是因为青野季吉的机械论为福本主义所乘呢,还是福本主义影响了青野季吉写了那篇文章,总之,目的意识论成了福本主义进驻文艺战线的一条通道。一个时期福本主义给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流毒深远,及于中国。
福本主义是日共领导人福本和夫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文艺思想或文艺理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它对于文艺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它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曾经一度为某些人所信奉,把它当成指导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方针。
福本主义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批判山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起来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山川均主要认为,在日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建立合法的政党,搞经济斗争。所以把他叫“解党主义”,取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他对文艺运动也有影响,后来的文战派就是支持他的。福本在日共决定重建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文章批判山川均,并且提出一套建党方法。由于他搬弄了“左”的马克思主义词句,迷惑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集体参加普罗艺术联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的成员,如中野重治、鹿地亘、谷一等人,都是拥护福本主义的。福本主义认为,当时日本的革命运动正处于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阶段,由于资本主义急速没落,革命已迫在眉睫。为了建立一个非常纯净的革命核心组织共产党,必须通过理论斗争,把一切工联主义、折衷主义思想排除出去,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才能结成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他有两个口号,就是“理论斗争”,“分离结合”。这种理论斗争和分离结合,不仅党要搞,群众团体也要搞,福本要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要通过理论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战斗意识。而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先结成主体,指导的集团,来开展这种理论斗争。
福本主义给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带来的危害,简单说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强调理论斗争,净化意识,分离结合,破坏了文艺上的统一战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组成第一个文艺团体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联盟,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重新结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两年多的时间内发生了三次大的分裂。第一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由普罗文艺联盟内被“分离”出一部分人,组成无产派文艺联盟。一九二七年六月普罗艺术联盟又一分为二,大批人马另组劳农艺术联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劳农艺术联盟又分离出一批人,另组前卫艺术家同盟。这样派系林立,内战不已,削弱了战斗力量。第二,助长了极左的机械论的文艺理论占了上风。如此,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他们认为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教化运动,是发动群众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而发展的教化运动。这就把文艺运动和政治斗争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还认为艺术是以政治上的暴露手段组织大众的进军号角,是对政治暴露起协助作用的具有次要意义的东西。艺术只是政治煽动的手段。他们对于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并且否认文学的艺术性。他们说:“无产阶级的激情,可以最率直、最粗野地大胆表现出来……它无视过去一切的艺术性”,“旧的形式和技巧,隐藏在抽象的语言中再现出来,不过是从根本上威胁着经过苦难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艺术”。象这样一些观点,由于福本主义,竟至在文艺运动中占了主导的地位。
人们说,福本主义对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有影响,这主要的表现也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文艺理论上的机械论。郭沫若说: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的原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
这说的是一九二八年以前的情况,但用它来说明一九二八年以后,也还是恰当的。福本主义以及日本的机械论的文艺理论,确乎是由一些人搬来中国,运用在左翼文艺运动上,而犯了错误。一些人疏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而喜欢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把福本主义那一套分离结合的办法拿来使用。他们也很欣赏意识净化,主张用无产阶级的意识批判一切,他们提出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学进行全部的批判,完全的否定。有一篇提倡革命文学的重要文章,在结尾说:“我这篇文章,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这里的“理论斗争”,不是一般的用语,作者特意打上了引号,可能是作为福本主义的一个公式的理论斗争。至于文艺理论上机械论的东西,留下受日本的影响的痕迹的东西,也是不少的。但这里留下一个间题。我们知道,日共的福本主义,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受到了清算。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共的问题,并就日本的革命作出了决议,这就是有名的《二七年纲领》。《二七年纲领》全面地分析了日本的革命形势,确定了日本的革命任务,在此基础上着重地批判了山川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福本和夫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二七年纲领》由藏原译成日文,于十月间在日本公开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就受了批判的福本主义,怎么可能还在一九二八年对中国的文艺运动发生影响呢?其实,日共当时对福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很彻底,而且没有深入到文艺战线上。文艺战线并未因为批判福本主义而受到什么触动,纠正什么倾向。那些执行福本路线的人也没有作过什么自我批评。况且批判福本主义的时间是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的,日共通过《二七年纲领》时间更晚,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所以这种批判活动未能波及到中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恐怕我们也不能说,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出现的一切“左”的偏向,都是福本主义影响的结果。当时,中国党也在执行一条“左”的路线,而革命文学的某些倡导者也有犯“左”的错误的思潮根源。福本主义不过是助长了他们原来就有的“左”的倾向。
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理论思想上曾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某些影响,总必须提到藏原惟人的理论。藏原惟人从一九二七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他基本上是反对福本主义的,对清除福本主义在文艺运动中的影响作了努力;虽然他的文艺思想间题也很多。他先是同青野季吉等人于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普罗艺术联盟排挤出来,组成劳农艺术家联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又从劳农艺术家联盟分离出来,另组前卫艺术家同盟。一九二八年主张成立各派无产阶级艺术团体的大联合的左翼总同盟。后来,又把前卫艺术家同盟和普罗艺术家联盟合起来,组成新的统一的团体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一九三一年,又建议解散“纳普”,另组成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叫全国协议会,由协议员组成。鲁迅与高尔基等被推选为名誉协议员,)他实际上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推动者,领导人。他的理论最系统,对日本影响最大。他的差不多的作品,中国都有译本。鲁迅说“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还是肯定藏原惟人的翻译工作的。又说:“钱杏邨先生近来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这是指钱杏邨引用许多藏原惟人的论点,写了《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文章,批评茅盾。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藏原惟人的理论,对于左翼批评家影响之深。

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1928年参加日共,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32-1940年入狱,战后参与重建日共的活动。长期担任日共文化部长。
藏原惟人是最早向日本介绍普列哈诺夫的人,他和外村史郎合译的普列哈诺夫的《艺术论》,就是鲁迅译本的底本。他的文艺思想是受了普列哈诺夫、弗里契以及“拉普”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文艺活动的初期更是如此。比如,他在日本文艺界争论作品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时,写的那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的文章,就是根据普列哈诺夫在《二十年间》的序文中的观点,认为文艺批评第一个阶段是分析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意识,第二个阶段是评论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一文中,一方面根据布哈林、波格达诺夫的理论观点,认为艺术是组织生活的东西,具有提高人们的生活并使之趋向一定方向的任务;但同时也认为艺术是对于世界的认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一方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另方面也主张真实地描写客观生活,以提高人们的认识。从这两个例子里,不难看出藏原惟人的文艺思想的渊源。
前面己经提到过,藏原惟人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曾写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自我检讨、也是藏原本人的文艺思想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为艺术理论的列宁主义而斗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与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有联系的六个方面的文艺理论问题。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站在列宁主义的高度重新探讨。这六个问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批评家与文学史家;文艺作品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藏原惟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在中国都有附合者和引用者,可以说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藏原惟人的文艺观点,较为系统,较为高明,在日本起了实际的指导作用;而同时,他所讨论的问题,已经超过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到一些创作上的具体问题和文艺运动上的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碰到的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藏原惟人的理沦,一方面是和在福本主义影响下的唯心论、机械论的文艺理论做一定的区分和斗争,另方面,他从坚持文艺必须是党的阶级的这一原则出发,而强调文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作家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对于迎接新时期的战斗任务,而欲克服过去理论上的错误和弱点,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针对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错误而加以批判,加以斗争”,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战斗力的左联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藏原惟人的许多论文都被译成中文,在三十年代的刊物上登载,有的文章甚至有两种译本。
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的大众化的提倡,是早于我们的,而且对我们有影响。藏原惟人是提倡大众化最力的一个人。在理论的主张上也还正确。他把大众化的问题,看成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中心问题。他批判了那种“最艺术的东西是最大众的,而大众的东西是艺术的”错误,也反对认为“单只客观地描写了大众的生活便立即成为大众的艺术”的说法。他所阐述的大众化的内容、对象、形式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实现大众化的具体办法,在我国大众化运动初期的一些理论文章中,看到了反响。当然,左联后来的几次讨论,比起日本来要广泛深刻得多。
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藏原惟人早年曾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艺术,都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从这个角度看,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这虽然不够正确,但他后来,既反对把二者机械地对立起来,也反对把二者机械地结合起来,而主张文艺和政治,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而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我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队伍在批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时,曾有人把藏原的这个论点当成理论武器。也认为,“文艺和政治是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统一了的,而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形式。”这里完全把藏原的话引用来了。
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藏原惟人理论活动的最光采的部分,也是他对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所作出的带有创造性的贡献。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他提出的较早,是他总结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特别是创作上的经验教训,把过去的指导创作的一系列理论加以发展而提出来的。为了阐释这个创作方法,他写了多篇文章,其中的《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中国有两种译本,《再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也翻译过来。从这两篇文章来看,错误的和不科学的提法当然是有的,但文章确实不乏一些好的见解。如主张作家必须客观地真实地描写现实,必须是现实主义者,但这种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不同。作家首先必须懂得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立场,用“前卫的眼睛”来看世界,来描写世界。因为现在能真实地、全面地、发展地观察现实的,只有战斗的无产者能做到。他并且最早地使用了形象、典型化等概念,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根据无产阶级解放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选取那些有用的东西,而舍弃那些无用的东西,偶然的东西,等等。这一口号提出之后,不仅日本的革命作家认真遵循,而且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关于创作方法作了这样的规定:“作家必须以无产阶级观点,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这显然是和藏原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联系。
《拓荒者》上有一篇介绍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章,其中说,自从把藏原惟人的《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翻译过来以后,除掉有个别人怀疑曲解以外,一般人都如日本一样,一致地朝着这个方向阔步向前的。可见,当时的左翼是大体上接受了个创作方法。
总括起来看,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潮,从它的发展来看,粗略地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阶段是以平林初之辅和青野季吉为代表,主要是讨论了文艺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一般关系,也接触了作家的应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受福本主义影响的时期,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理论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很严重。第三个阶段主要以藏原惟人的思想理论为代表。它的特点,先是想抵制福本主义的影响,接着又力图摆脱普列哈诺夫、拉普的影响,但终因时代的限制,而没有达到目的;但对于运动却起了指导的作用。这三个时期的思潮、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我国的左翼文艺。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大体上以一九三二年为界,在这之前,所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不只是福本主义,而且也包括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等人。而这种影响,又和普列汉诺夫、弗里契的影响,波格达诺夫、德波林的影响,拉普的影响,紧紧地交错在一起。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后,逐渐减弱。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论战时,有更多的人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这一场论战也暴露了左翼理论家的弱点;但总的说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www.syxtk.com/wzzx/llyd/wh/2016-04-18/37312.html-红色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