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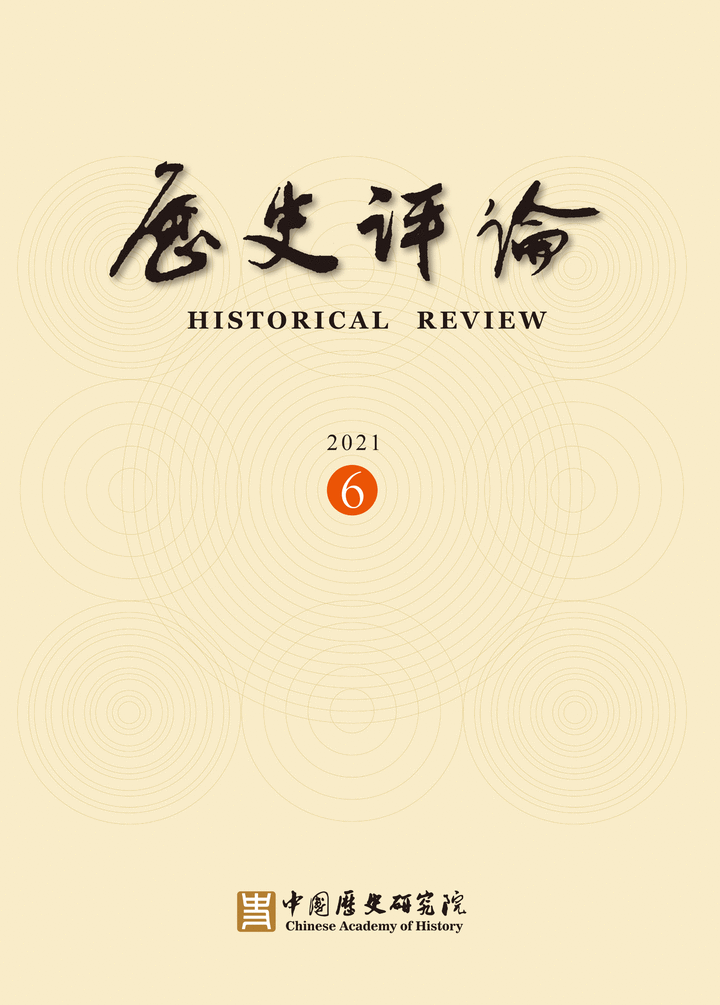
晚近30余年来,由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帝国、支配世界经济的美元本位、宣称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制、自生自发自律自制的市场经济所支撑的西方文明,已渐呈颓势,老态毕露。就此而言,历史远未终结,人类社会在寻求崭新的21世纪文明形态。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外交官员兼兰德公司学者、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已经是人类社会最好的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再无其他可能。太阳底下无新事。福山的断言只是照猫画虎,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口头禅“除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翻版。任何一种理论的命运,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今天再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它已经被真正的历史所“终结”了。
“政体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晚近三十余年来,人类社会进程中无数代价沉重、教训深刻的历史事实表明,福山“历史终结论”所含的“政体终结论”和“经体终结论”,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迷思。我们先看前者。
“政体终结论”将“转型范式”变成后冷战时代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思考路径。既然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成为政治上的唯一选择,那么,所有与自由民主制不同的政体,都必将通过政体转型,转向以多党定期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自由民主制。而且,这种转型并不需要考虑该政治体的政治历史、经济状况、民族性格或文化传统等结构性因素,只要政治精英有意愿、有能力,所有的好事就可以一夜之间到来。简言之,“转型范式”主张,民主转型优先于国家建设。
“转型范式”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威风”了十年,很快就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宣告失败。的确,在这十余年的转型时期中,约有100个政治体发生了政体转型,并且大都以美国政体为模板。但转型的结果表明,只有不到20个政治体在转型后相对稳定,其余大多数政治体都被迫接受了西方国家强加的苛刻条件,转向了既不负责任又没有效率的美国式多元主义政治,从而陷入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灰色地带,又因为治理失灵而退化成“失败国家”。这又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苏东国家“颜色革命”的导火索,打响了恶斗不止、动荡不堪、代价沉重的“选举战争”。
在紧随其后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北非、东南亚、西亚地区相继爆发了类似的街头运动。埃及总统穆尔西、泰国总理英拉、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等“民选”的国家或政府领导人,相继被街头运动拉下马,新组建的却仍是军人政府或寡头政府。菲律宾发生震惊世界的选举屠杀惨案,印度尼西亚国会废除地方首长直选,马来西亚围绕总理人选爆发政治危机。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多党定期竞争选举的政治选拔机制备受挑战,自由民主制的正当性危机空前严重。
“政体终结论”的破产,在转型国家如此,在所谓老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晚近四五十年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上层阶级主导的利益集团,既是各级政府官员候选人的主要捐助人,又是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政策和法律议程的设置者,还是政治体系输入和输出两端的把持者。他们时刻阻止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出台,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因此成为痼疾。所谓自由民主制,早已暴露了其金权民主、金融寡头专政和寡头统治的本质,这一点渐成西方社会各界共识。
连“休克疗法”发明人杰弗里·萨克斯都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 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把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寡头政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1%有、1%治、1%享”(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已然取代了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推动美国从民主制变成金融寡头专制,从民主政治变成了金权政治。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99%的美国大众对金权政治的反抗。政治学者约翰·麦考米克也认为,自由民主制实质上是排斥阶级因素的选举寡头制。代议制研究专家汉娜·皮特金提出,代议制扩大了少数富人的权力,将自由民主变成了金钱民主。法学家拉尼·吉尼尔认为,一旦选举变成富人或权贵操控政治的游戏,普通人丧失政治影响力,公共官职就成了代表的财产,代表成为权贵,代议制民主失去问责能力。
因此,就连福山本人近十余年来也开始呼吁,美国应该废除代表中上富人阶层利益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建立民主独裁制,以图解决当前美国的重重困境。而特朗普的当选,也意味着美国政治的百年轮回、由盛而衰,从“商人干政”转向“商人执政”,堪称“金权政治”在美国的全面复辟。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严重缺乏适应性、回应性、正当性,备受拷问、陷于窘境。
究其根源,正如政治学者谢尔登·S.沃林所言,美国所代表的所谓自由民主制,旨在通过消解人民的权利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这也正是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美国的所谓分权体系将人民隔绝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体系之外,这样一来,人民就空有普选权,而实际上无力对抗那些资产者。
环顾当今世界,从亚洲、非洲到欧美,历史正无情地宣告:“政体终结论”已然破产。
“经体终结论”的幻灭
在经济与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程度愈益加剧的当今时代,不仅“政体终结论”破产了,福山关于经济制度的“经体终结论”也幻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欧美列强在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挑战下不得不放弃殖民体系,被迫将其工业化与殖民体系脱钩,开始“去工业化”,紧接着又受到非西方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挑战,国家实力开始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延续了40年的“高税收、高福利、高开支、低增长”社会治理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再生产模式,与社会老龄化加剧相结合,催生了近十年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发展停滞,中产阶级萎缩,顶层富人财富大增,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社会共识。
在此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加,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所引领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这进一步凸显了“经体终结论”的荒谬。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所谓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兴起和发展,高度依赖军事—财政模式,以经济增长、军事实力、殖民主义和政府效能为“火车头”,建立了对非西方世界的霸权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格局相对稳定之后,经济增长、继而更公平的增长先后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火车头”。在这个时期,通过社会革命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更广泛的政治民主、更公平的经济民主、更合理的国际民主,也被视为政治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火车头”。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家制度能力的更高要求,国家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内外挑战发生的新变化,国家间竞争的现实和长远、内在与外部需要,都决定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为“火车头”,如此才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实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这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国家,才能在不同发展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抉择。在国家初创时期,要实现国家整合、民族独立,通过革命推动现代化,提高政府效能,提高干预、渗透、监管社会的能力,增强军事实力。同时,要不断推进国家建设,实现经济增长,推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更广泛的民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改善生态环境,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还要摆脱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强加的依附地位,防止商品交换逻辑渗透社会政治生活,保持内外一致的国家自主性。这些目标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必须作出权衡抉择,依据自身能力确定在特定阶段所能实现的一个或多个目标。
政治经济学者乔万尼·阿瑞吉指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能否告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条矛盾重重的“老路”,能否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能否让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生态之间更平衡又可持续地发展,能否消除经济成功背后以收入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矛盾,是人类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经体终结论”显得如此单薄、无力,如阳光下的肥皂泡一般幻灭于无形。
人类文明新形态初露曙光
在过去400年间,人类社会的文明主要是由西方世界定义的。所谓19 世纪文明仰赖于欧洲势力均衡体系,20世纪文明则仰赖于美苏对峙这一升级版的全球势力均衡体系。20世纪文明所铸就的世界总体和平,从1945 年至今已延续70余年。
然而,晚近30余年来,由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帝国、支配世界经济的美元本位、宣称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制、自生自发自律自制的市场经济所支撑的西方文明,已渐呈颓势,老态毕露。就此而言,历史远未终结,人类社会在寻求崭新的21世纪文明形态。按照上述阿瑞吉的思路,70余年来,具有鲜明人民性、高度自主性、灵活适应性和巨大创造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是走向国富民强的正确道路,既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关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更事关人类社会的前途。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于世界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人类社会只有摆脱“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和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迷思”,让经济从属于政治、文化、社会所构成的总体关系,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持之以恒地缩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才有可能建构起更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进而开创新的文明形态。
其次,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城市和信息诸领域的现代化努力,不仅消灭了绝对贫困问题,缓解了相对贫困问题,提升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推进了各阶层之间的共同富裕水平,而且以切实行动帮助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减少贫困人口,进而减少了全球贫困人口。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于世界的第二重意义。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凸显了具有鲜明人民性、高度自主性的政党领导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国实力的进退兴衰决定了世界格局的演变,竞逐富强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既需要高效廉洁的官员队伍来执行决策,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兼具专业性与人民性的警察力量来维护社会安宁,又需要汲取社会资源为国家运行提供财力,需要塑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共识,需要识别公民的身份和财产信息,进而建立包括监管、再分配和税收等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还需要吸纳不同阶层的参与诉求,通过公共政策整合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短期利益、部分利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尤其需要拥有战略意识、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遂行能力的政治领导群体。而上述这些,都离不开拥有强大理想信念、保持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现代政党制度。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于世界的第三重意义。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各阶层普遍关心、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处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所面临的、必须回应的内外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开创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
概言之,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世界是天下人的世界,不是西方人一家之世界。非西方世界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开辟更多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民族走出的这条新路雄辩地说明,历史并未终结,它就在探索者脚下、就在奋斗者手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www.syxtk.com/wzzx/llyd/ls/2022-03-01/74127.html-红色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