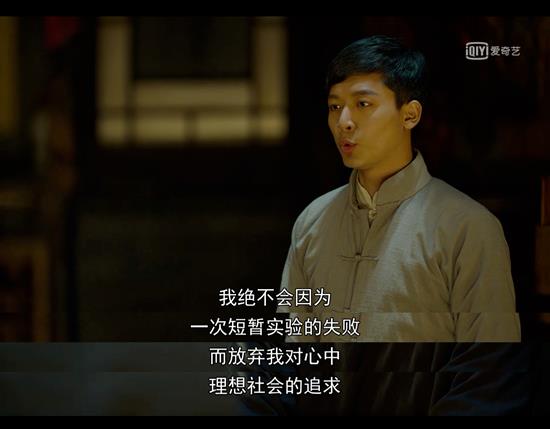《觉醒年代》剧终:革命尚未完结,同志仍需努力
《觉醒年代》剧终:革命尚未完结,同志仍需努力
淋 署
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近日迎来了大结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漫长的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的时期。令人鼓舞的同时,这个结局也不无悲凉之意,因为剧中字幕清楚标出了众多革命者的归宿:死亡、牺牲、英年早逝。
作为近年来罕有的、引起了颇高讨论热情的革命历史剧(豆瓣评分达到9.2),《觉醒年代》确实有着多层次的突破意义:对陈独秀、蔡元培、辜鸿铭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呈现等等。更重要的是,对不少青年观众来说,《觉醒年代》令革命的激情重新变得可亲、可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也不再是“情怀党”的无聊空谈。然而,其“主旋律献礼剧”的定位,也决定了这部电视剧无法超越的意识形态限度,比如用民族主义话语吸纳和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内涵的倾向。
前几天,“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表示:意犹未尽的观众们不必再催促《觉醒年代》加更续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本文则意图追问:革命是否已然完结?什么才是召唤革命幽灵的“正确姿势”?怎么办,才能不辜负革命先辈的亡灵?
01
自由主义失败之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觉醒年代》将其开篇设置在了1915年,这无疑是一个深具意味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个年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辛亥革命建立起的共和制度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这些事件共同凸显了一个时代主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经典”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也在当时思考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趋于弱势。
一战所显现的欧洲危机,从其爆发的1914年开始便刺激着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欧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场战争是民主vs.专制吗,抑或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内部竞争所致?而中华民国自建立以来的共和危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乱象——也活生生展示着代议制民主是如何沦为政党政治权斗工具的。人们慢慢意识到,这是中国的问题,却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代议制民主与绝大多数的国民有什么关系,这个体制真的能代表国民的声音吗?
更为赤裸地向国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暴力的,是日本。同样作为被西方殖民者敲开国门的国家,日本成功地现代化,实现了“脱亚入欧”;所以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被视为中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楷模。彼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在中国也颇有市场:全亚洲联合为新的强者,从而对抗欧洲的想象,怎能不激动人心?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国人才如梦方醒:大东亚主义只是换了张脸的帝国主义,而日本的现代性也只是换了张皮的西方现代性。1915年的《二十一条》则更加深了对日本的幻灭。对日本现代性的怀疑正是留日学生普遍激进倾向(如李大钊、鲁迅)的来源之一。
自由主义的破产,使得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一条向右,一条向左;一条望向自身民族的过去,一条朝向人类共同的未来。这就是《觉醒年代》用大量篇幅呈现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派”与“保守派”的论争。《觉醒年代》提醒观众,这一时期的“保守派”绝不仅仅是一般印象中腐朽的满清遗老;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具有充裕的“现代性”,接受了西方或日本的现代教育,并且能够娴熟地调用反西方、反现代性话语来宣传保守派思想。《觉醒年代》第一集中,留日学生中的保守派指责激进派的话术就是“照搬美利坚民主共和制度”、“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今日舆论场域中的类似话术)。甚至连复辟的张勋在溥仪面前也懂得说一句“皇上,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啊”。
当然,《觉醒年代》中刻画得最为丰满的保守派人物非辜鸿铭莫属。作为爱丁堡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校友,辜鸿铭精通西洋文化。剧中,胡适在北大演讲时引用了《荷马史诗》,被辜鸿铭当场打断,后者嘲笑胡适不会讲希腊语、也不会讲纯正英国口音的英语。事实上,保守派对新文化有许多类似的指责。例如,保守派的重要刊物《学衡》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观点: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文化背叛了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既然西方时髦都是回归古典了,中国人也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i]。保守派的意图是证明自己的“旧”其实比新文化运动更“新”[ii],以争夺年轻一代的追随。
02
与保守派和解:今日民族主义如何再造历史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派和保守派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危机和自由主义破产的反应,也都具有某种反对西方殖民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两者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官方解释中,都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的历史选择。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水涨船高而“社会主义”内涵日益模糊的今天,两派的死对头却在《觉醒年代》中想象性地握手言和了。当然,这一“和解”的发生是以再造、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为前提的。此种对保守派思想的重新评估,实际上暴露出今日民族主义的右翼性质。
比如,电视剧多次(不无生硬地)让陈独秀和李大钊表态,声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全然否定。陈独秀说他“只反对三纲五常,不反对孔孟”;“只反对政治尊孔,不反对学术尊孔”。为毛泽东送行时,陈独秀甚至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他绝不全盘否定,“等将来国泰民安,我还想在故纸堆里安度晚年,多么惬意!”。一旁的李大钊竟也表示“我跟你愿望出奇地一致”。(所谓“想在故纸堆里安度晚年”已经成为后革命年代的革命历史剧惯常使用的一种陈词滥调:2007年电视剧改编版“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中,共产党人江华对林道静表示“完全理解余永泽(原红色小说中“保守文人”的代表)的人生选择”,并说自己“也想钻故纸堆,只是现在条件不具备,等将来建成一个新世界,自己还想向余永泽请教学问呢”。后来,林道静也安慰心灰意懒的余永泽:“你的知识将来国家用得着”。[iii])《觉醒年代》接近尾声时,李大钊又带着学生们一起来参观韩愈祠,抒发他对儒家教育的满腔尊崇。由此观之,陈李二位实在是“通三统”[iv]学说的祖师爷啊!
平心而论,新文化阵营内部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与陈独秀相比,曾提出新旧折衷论的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确实没有那么抵触。并且,正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的,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培育了李大钊一种髙度的侠义气质、一种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迫切愿望。李大钊后来的生涯确凿地证明,这些中国的传统能够为激进的、反封建的目的服务[v]。如果说李大钊的相关部分尚有某种历史真实性,那么将言论最为激进的陈独秀也塑造成一位“理中客”,只能说是编剧对历史的魔改了。
相应地,剧中也极力凸显陈、李的反西方色彩,并试图让他们在这一点上与保守派达成和解。第十二集借用了北大解聘英国籍教授引发外交争议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但添油加醋地杜撰了一个与英国人谈判的“教授团”:蔡元培让陈、李去说服辜鸿铭参加教授团,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打败英国人。在谈判桌上,辜鸿铭大发宏论,说中国人如何比西方人更文明、更优等。然而,辜鸿铭及其“中国人的精神”论无非是一种内化了西方视角的自我东方主义。所谓“西方人是物质的,中国人是精神的”等等庸俗的比较文化理论,貌似颠覆、实则重复了白人至上的种族结构。
对西方貌似颠覆、实则重复的话语渗透在今日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方方面面。民族主义者的普遍理想是让中国成为高仿欧美现代性的复制品,一幅强大到超越了欧美“原画”的赝品。不必奇怪,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以目前世界的强权——西方——作为自己的范本与镜像。与之伴随的是第三世界和国际主义视野的消失。例如,巴黎和会上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引发了全球的抗争浪潮[vi],但只有五四运动作为反帝爱国运动被高高举起,而1919年同期发生的朝鲜、埃及、印度、中东、美国黑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运动却鲜少有人提及。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历史课本上,只有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第三世界的踪影悉数蒸发、无迹可寻。
今天,甚至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被理解为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可以用完即弃的历史“工具”,而不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所谓“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救亡图存之振兴,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觉醒年代》中塞给李大钊的台词)。作为对照,我们不妨重温真正由李大钊本人所写的一段话:“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指法国大革命),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指十月革命)。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03
革命阵营内部的论争:托派与无政府主义
幸好,《觉醒年代》在“回收”保守派历史的同时,也“回收”了曾被遮蔽和压抑的一部分革命历史。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陈独秀是一个有争议并尽量避而不谈的人物,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期转变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主流革命路线有很多批评。虽然《觉醒年代》并没有触及后来这段历史,其仍是第一个全方位展示了陈独秀形象的中国影视剧。
当然,《觉醒年代》中更引人注目的革命阵营内部分歧,当属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剧中讲述了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共产党人的无政府主义“前史”(多次提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生动地呈现了无政府主义实践“工读互助社”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
不过,剧中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对立的处理,却与史实不符。1921年之前,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蜜月期”(或说混淆期)[vii]。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190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恩格斯为该书写的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本,发表在《天义报》上,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出版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同年,《天义报》刊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译文。
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早(晚清末年),早期影响力也较大;相比之下,对于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仅仅是西方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十月革命以前,即列宁主义阶段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当时的中国缺少这些条件,因而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对政治行动的指导意义。
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三到四年中,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野也远非那么清晰。十月革命发生后,世界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多表示了支持态度,认为苏维埃可以很快过渡到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积极介绍十月革命:1918年4月,无政府主义杂志《劳动》发表了两篇论十月革命的文章,这是当时中国发表的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思想的最详尽的报道。《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多次督促儿子陈延年研究十月革命,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陈延年则声明他对十月革命不感兴趣,因为那是“暴力革命”——此种剧情设计也体现出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多种流派,其中只有受到托尔斯泰影响的一派主张彻底的非暴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扩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绝大多数共产党创立者(除陈独秀外)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一个无政府主义时期。
1922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历了悲剧性的分裂、相互的诋毁和攻击。这一分裂部分起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1927-28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无政府主义者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其中一小部分(如吴稚晖)参与了针对共产党的“清党”行动,这确实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上甚不光彩的一页。而在1928年后,那些真诚信仰、实践无政府主义的人士也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作为社会运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此夭折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此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成功,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无政府主义便毫无价值——这样会陷入一种胜利者的、强者的逻辑,也正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正如《觉醒年代》中陈延年在工读互助社失败之际饱含情感的发言:“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在社会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家庭-性别问题等方面,无政府主义都有着持续的激进性,有助于恢复和唤醒被“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遗忘、所玷污的乌托邦理想。
04
历史的双刃性——让革命重焕青春!
也许《觉醒年代》最令人触动的,是那一代“新青年”炽热的、洋溢着理想的、勇于实践的革命青春。或如陈独秀所言:“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研究室与监狱》);或如网友们所言:这剧,看了让人想革命。《觉醒年代》让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在中国荧屏上重新焕发光彩。
青年和青春曾是革命中国的突出主题。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青春”变为一种消费主义和欲望经济的符号。如果说革命青春指向的是未来的理想,那么后革命青春则困于封闭的、转瞬即逝的当下。如今的中国青年人人感叹“青春不再”、“未老先衰”,这是我们时代的病症,也正是《觉醒年代》这类作品在青年中流行的原因:那里面有我们所匮乏的、真正的青春。
革命历史的双刃性也由此显现。一方面,革命历史当然可以用来背书当下的合法性——所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这盛世如你所愿”是也(此句出处正是微博网友对周恩来总理说的话)。今年春节期间也有一条热搜曰:#李大钊曾孙希望曾祖父看到今日中国#。我们可以在荧屏前掉几滴眼泪,然后安慰自己:革命的事业已然完成了,逝者的灵魂可以安息了。但另一方面,回顾历史总会在不期然间召唤出革命的幽灵,让我们去继承前人的理想、去继续那前人未完成的革命。是的,如果死者将被救赎,这也只有通过我们在当下的行动才能实现:将他们失败了的、为正义而战的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如何悼念革命的先辈?是发两条弹幕“这盛世如你所愿”、“泪目”然后继续我们996的、未老先衰的所谓“幸福生活”,还是像他们一样,走到工人、农民、女性和少数民族中间去,和被损害、被压抑者站在一起?且用罗莎·卢森堡的遗言作为结尾: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参考文献:
[i]刘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ii]汪晖:《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
[iii]刘复生:《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
[iv]甘阳:《通三统》
[v]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vi]Margaret MacMillan: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World.
[vii]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www.syxtk.com/wzzx/djhk/wypl/2021-04-04/68518.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