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被视为打开学术宝库的一把钥匙,“于20世纪开始步入理论目录学的发展阶段。它已经走过了科学发展的完整的历史过程,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目录学之所以到20世纪早期能从校雠学、版本学等相关学科中剥离出来,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既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目录学自身发展与演变的产物。其中,目录学家对于目录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代目录学是连接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之间的纽带,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对于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学术遗产的整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作者全根先
一、目录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由于目录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非但没有人为目录学下过确切定义,许多著名的目录学家甚至否认目录学的独立存在。例如宋代的郑樵、清代的章学诚等,认为目录学是校雠学的一部分。章学诚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定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章学诚所说的校雠学,实际是广义的校雠学,包含了校雠学、目录学的内容,不过也反映了目录学未曾从校雠学独立出来这一事实。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一书中,撰有《中国无目录学》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无目录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大体说来,有以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国垣《目录学研究》为代表的史的目录学家,有以叶德辉《书林清话》、孙毓修《中国版本源流考》、柳诒徵《中国版本略说》为代表的版本目录学家,有以刘咸炘《目录学》、《校雠述林》,张舜徽《广校雠略》、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为代表的校雠目录学家,还有以姚名达《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为代表的“中西合璧”式的目录学家。乔好勤先生曾将这一时期目录学研究归纳为旧派、新派、新旧俱全三派;而究其实质,不外乎以叶德辉、刘纪泽、余嘉锡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派,与以梁启超、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杜定友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尽管他们所持观点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目录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姚名达可以说是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在《目录学》一书中,他在吸收前人目录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目录学思想。他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又说:“目录学这种学术,是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书籍,一一考察它的性质,分成许多种类,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在一定的地方,再编成一种目录,使得看书的人先查目录,可以知道书籍的所在,明白书籍的大概,决定应该看什么,应该在什么地方找。这种目录不但应该有书目,把书的名称、著者、册数、出版地点、出版年月告诉读者,而且应该有叙录,把书的主要篇目、内容大概、著者生平、版本好坏等等有关系的事情,用极简明的文字告诉读者,使读者不但知道某书在那一类,某类有什么书,而且明白某种学术应该读什么书,某种书籍值得读不值得读。象这样,才是目录学的正轨。”在这里,他不仅给目录学下了定义,同时也确定了目录工作的范围。
汪国垣在《目录学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以往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把目录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四类,并指出“藏书家之目录”重视版本,“读书家之目录”重视提要,“史家之目录”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家之目录”则认为目录学为“簿属甲乙纲纪群籍”之事。他给目录与目录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方足以当之。”杜定友虽然提出“中国无目录学”,但是他又主张:“目录学者,图书簿记之法也。所以便检查而利求学,故有其目必有其书,有其书即可究其学。”“故有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字典式目录、分类目录,多至数十种。而我国旧日目录学,惟分类目录一种而已。”由此可见,他所说的“中国无目录学”,其寓意是要建立新的目录学。

二、明确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古代,由于目录学与校雠学、版本学等多个学科联系在一起,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不很明确。近代目录学家姚振宗曾说:“目录之学,言其粗,则胪列书名,略次时代,亦不失其体裁;言其精,则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各具渊源,版椠之古刻今雕,显有美恶,与夫纸墨优劣,字画精粗,古之人亦不废,抉奥提纲,溯源散委,盖实有校勘之学,寓乎其中,而考证之学,且递推递密至无穷尽也。”在他看来,目录学必须有版本、校勘、考证学的辅助,一部好的书目应该鉴别版椠优劣,校勘异同,考证讹谬。他还说:“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他本人的目录学著作,如《汉书艺文志条理》《隋书经籍志考证》等,都是穷校勘、竭考证、通版本之作。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引进,区别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已成为目录学家的自觉行为。
目录学与校雠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姚名达认为,目录学与校雠学虽有密切的联系,却不能等同。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他指出:“目录学与校雠学有关,但重其篇卷之整理而忽其字句之校雠。”校雠“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错误而言。然自向、歆领校秘书,始将流动不居、乱杂无序之古书,编定目录以固定其性质。晋世荀勖、宋世谢灵运,皆尝受诏‘整理记籍’。故校雠之义即为整理”。他还说:“校雠之义,近乎整理,非只校勘字句……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古之书籍,未经校雠,难于著录,故两事相因,不易分辨。”从现代学术分科观点看,“则刘向之事近乎校雠学,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纵使歆亦校书,向亦有目,要其精神各有所重,学术断然分途,可无疑也。”这就为将目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郑樵《通志·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说:“观其类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见矣。”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近代目录学家也注意到了这点。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全史也。”汪国垣认为:“目录之学,与史相纬;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源流,及一家一书之宗趣。”正因为如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但是,两者又有各自的研究重点。蒋伯潜在《校雠目录学纂要》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说:如果说“部次条别”“著录部次”属于目录学的范畴,那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则更多是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了。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目录学的特定的研究对象?杜定友认为:“目录学之对象为图书。”在他看来,目录学的基本功能,就是为读者提供检索、求学的路径,而“我国目录学,其原理为考镜源流,未尝为阅者设想”。有必要指出,杜定友所说的目录与书目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图书馆的各种卡片目录是目录,研究其编制方法为目录学。而中国古代的各种目录,他称之为书目,究其学者为书目学。书目之编,以书为目,其学不限于一科一门,其书不限于一时一地,此乃书目与目录之最大区别。他还提出了目录学的基本原则,即:藏书目录有其书必有其目,有其目必有其书;目录惟便检查;目录必记明书次,以方便即目求书;检查目录必用直接方法;编次必有规则;目录必用活页,即卡片。另外,他还将目录分为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字典式目录、分类目录等十多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近代目录学与传统目录学之分野。

三、强化目录学的社会作用
对于目录学的作用,历代学者多有论述。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学是)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章学诚在“六经皆史”“道不离器”的哲学、史学思想指导下,撰写了目录学巨著《校雠通义》,强调目录学的作用,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近人张之洞则认为目录学是“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虽然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大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论述。具体说来,目录学于社会而言,则有助于学术文化的整理与传承;于个人而言,则有助于读书治学。事实上,目录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对过去学术文化进行整理的结果。至于其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说:它是“研究学问必备的常识”。
到了近代,维新派将目录学的社会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作为一部辨伪目录学著作,从理论基础上向封建正统思想开了第一炮,吹响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号角;其介绍西学之作《日本书目志》,则成为他向光绪皇帝进呈,敦促其放眼世界、锐意改革的书目著作。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强调:“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为了加速西学的传播,使西书能迅速地让国人了解并方便阅读,只有通过目录学这一捷径。他说:“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其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由此可见,目录学在他的心目中,其地位与作用已超越了传统目录学的范畴。在编纂《图书大辞典》时,他为目录著作单独设立一部类,名为“簿录之部”。维新派对于目录学作用的宣传,促进了目录学学科地位的确立。
当然,更多的学者是从学术角度来探究目录学的作用。余嘉锡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目录学的作用是“辨章古人之学术。”这一观点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一致。他结合目录学在辨伪、考据方面的作用,认为目录学的作用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因此,“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至于目录如何才能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认为应从分类、编目、著录等入手,而余嘉锡则主要从书目著作体制特点方面加以论述,即“篇目用于考一书之源流,叙录用于考一人之源流,小序用于考一家之源流”。
姚名达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学术日益进步,书籍日益增多,在读书治学上“目录学就是唯一最有用的工具。”“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故分言之,各种学术皆有其目录学;合言之,则目录学实负有指导各种学术之责任。浅言之,将繁富乱杂之书籍编次为部别州居之目录,使学者自求之,目录学家之职务也。深言之,不特使书籍有一定之位置,且能介绍其内容于学者,使学者了然依南针以前趋,尤目录学家之功勋也。”他明确主张:“我们现在要唤醒沉迷,转变方向,使得目录学能够领导一切学术向新的未来世界前进,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说,姚名达对于目录学社会作用的阐述更切合现代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实际。

四、汲取古典目录学之精华
(一)目录学之变革
目录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从催生近代目录学的角度论,古典目录学中与时俱进的变革思想尤为重要。在我国古代,书目基本上都是分类排列的。刘歆作《七略》,既标志着古典目录学的诞生,也标志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的创立。此后,历代目录学家无不重视研究图书分类。虽然“七分法”“四分法”是图书分类的主流,但是对于图书分类问题的探索却从未停止。正如余嘉锡所说:“夫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可随之而变”,故“四部可变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致于百乎?”汪国垣也说:“学术随时代而变化,故著录之体例,不能一成不变。魏晋以来,学术日歧,典籍弥众,《七略》所部,已难尽遵。于是不得不别用概括之法,出附庸为大国,纳细流于巨川,而四部分类之法,遂得以乘时而起。”古典目录学发展中所表现的这种变革思想,为近代目录学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二)书目之多样性
一门学科要健康发展,不仅需要顺应社会与学术发展的潮流,也需要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始终保持其发展活力,与目录学家对目录体制、目录形式坚持不懈的探索密切相关。余嘉锡认为,古代书目可以分为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第一种类型的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第二种类型的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第三种类型的书目,如《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他还说:“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当然,书目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如郑樵、胡应麟根据书目收录范围,将书目分为总目、家藏目录、文章目、经史目;龚自珍、周贞亮、李之鼎根据书目编者,将书目分为部录(官修)、编目(私藏)、补志(史志);汪国垣根据书目功能,将其分为目录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这种书目类型的多样性,为近代目录学家所继承,也成为近代目录学的一大特征。
(三)佛教目录之发掘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佛经不断地被翻译成汉文,逐渐成为古代图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从东晋道安编撰《综理众经目录》开始,历代僧侣编撰了大量的佛经目录,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以往的目录学家对于佛经目录少有关注,更不用说吸收其目录学研究成果。梁启超是对佛经目录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优良传统的第一人。梁启超认为,佛经目录有五大优点,即:“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二曰辨别真伪极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搜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通过对佛经目录优点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普通目录在这些方面相差甚远。他说:“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梁启超对佛经目录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姚名达所说:“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墟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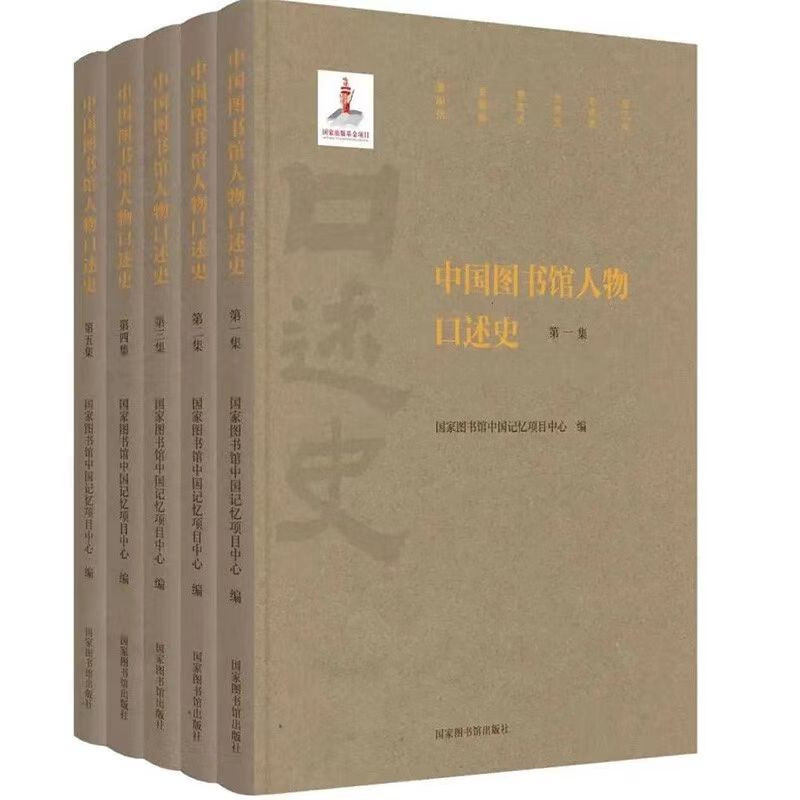
五、目录学方法的重大创新
中国古典目录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形成了一系列实用有效的目录编制方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挚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这种在书目中撰写总序、小序的方法,对读者厘清学术渊源、知晓书目大概十分有益。又如,互著与别裁两种编目方法,在近现代目录学中依然采用,前者如图书分类表中的类目互见法,后者则为类目参见法。再如重视撰写书目提要,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中说:“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其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他认为编目应当重视解题(即提要),并主张编制提要式目录。这些都是古代目录学家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而近代目录学家在继承古典目录学之优良传统、汲取西方目录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重大的突破与创新。
近代目录学方法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图书分类上。近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可以追溯到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对四部分类体系的突破。而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初版名《中国书目十类法》)的编制,则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该分类法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为中文书而编的新型分类法”。此后,新型的图书分类法蜂拥而出,当时相继编制了几十部“仿杜”“改杜”“补杜”十进分类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等。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在我国分类学史上开创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之先河,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独创了图书的九分法,最终结束了中国图书的四分法时代。”这些新型图书分类法与传统图书分类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们都是独立于任何具体书目之外的分类法,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指导,采用全新的学科分类体系,并运用参见类目、多重列类、仿分复分、类目注释等多种先进的编制技术。
编目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与图书分类法的变革具有同等重要意义。近代目录学家在编目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是借鉴和吸收中西目录学研究成果的结果。如梁启超重视佛经目录优点的发掘,余嘉锡、姚名达强调提要的重要性,是对我国传统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而杜定友、刘国钧等人则在吸收西方目录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编目思想。杜定友建议图书馆编制八种类型的目录以便应用,包括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种类目录(相当于现在的主题目录)、分类目录、参考目录、分析目录、字典式目录、书架目录,并提出必须编制一部统一的编目条例。他于1921年编制的《中文图书编目法》,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图书编目条例。刘国钧提出图书馆一部完全的目录应该包括字典式目录、分类目录、登录簿、排架目录四种,并将著录事项定为九种,即:书名、著者姓名、版本、版次、书形、标题、附注、提要和索书号码;在著录中,可根据不同的目录确定其详略。1929年,他还编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这些近代编目方法的创立,不仅对当时图书编目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中国近代目录学家在理论目录学研究方面成就非凡,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成果,架起了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之间的桥梁。从中国传统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的转型,其实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五千年而长盛不衰、愈加辉煌,正是因为其海纳百川、革新图强的优良传统。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