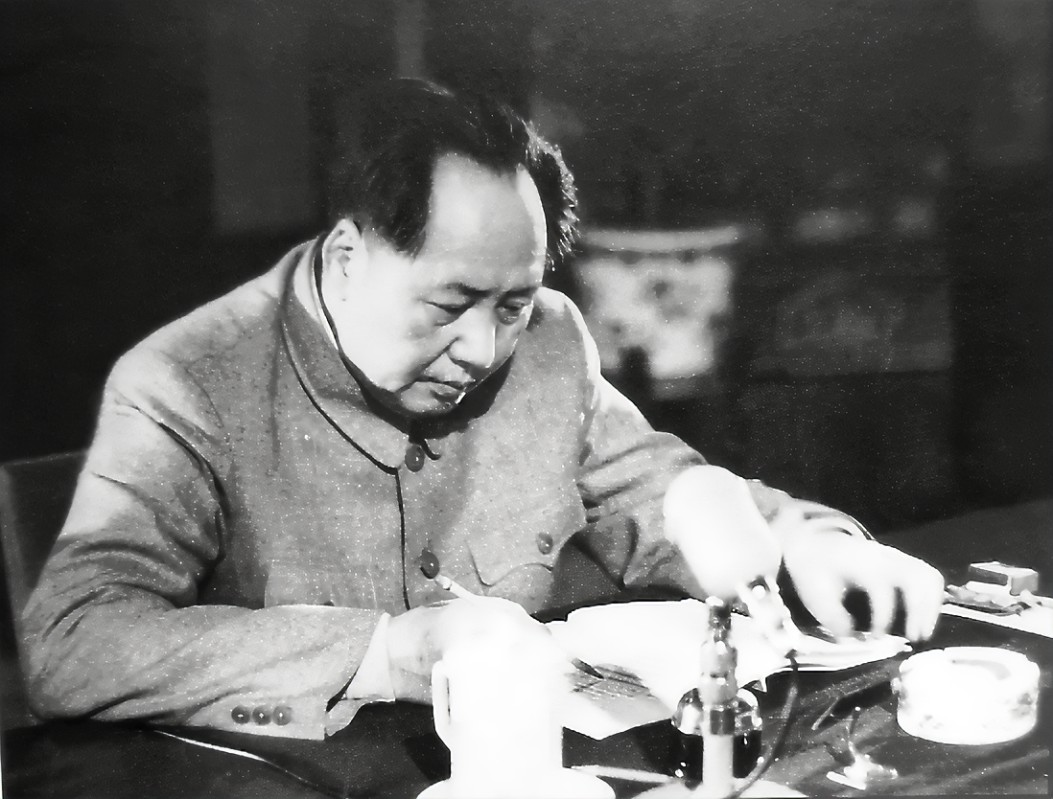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开版除了广泛收集原内部版未曾编入的文稿外,对文稿内部版出版后发现的问题逐一核校改正,对所有文稿认真研读,从疑必考,寻绎辨正,以确保文稿公开版的准确性,这是文稿修订、增补中的一项费时且十分重要的工作。
订正文稿中的差错对于深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编入的文稿存档多在半个世纪以上,其中发生种种错讹是难免的,这就需要编辑者对文稿进行认真的校勘和考订。特别是很多落款只署有月日或日期的文稿,虽然档案中有年代标注,但往往也有错情;个别文稿虽明确写有年代,但作者也偶有笔误;还有一些文稿档案的附件错位,张冠李戴,等等。因此在文稿编辑的过程中,对文稿的年代和时间的判别,以及对文稿文字的校勘,都是编辑者考订的主要内容。在文稿编辑工作中,是如何发现并对存疑文稿进行考订的呢?这里举要如下。
一、从文稿所述内容中求证
考订文稿的年代,尽可能使文稿不出现年代的错位,是考订工作的重要方面。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编辑者看到绝大多数文稿的档案年代是准确的,但由于一些文稿的落款时间只有月日或只有日,个别文稿甚至还没有日期,以致造成了文稿档案年代的差错。文稿内部版、拟增补编入公开版的文稿中都有不少这种情况。
通过认真研读这类文稿的内容,考察其中所述的史实、背景与档案年代是否相符,进而发现疑点加以订正。如《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的信》,这一文稿的落款时间没有年代,只有“六月二十三日晨三时”。文稿中说:“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听取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文稿内部版以档案标注的年代确定为1955年。根据文稿所述内容,编辑者逐一予以求证:一是未查到文稿中所提1955年这天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相关议题;二是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5年这天毛泽东是在从长沙返回北京的专列上,晚七时半才回到北京。当晚九时半虽召开了会议,但并非政治局会议,也无此议题。因此,这一文稿的年代就存疑。那么,这一文稿究竟写于何年呢?编辑者又进一步查找文稿中提到的陈毅的报告,先后从《陈毅传》和《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中得到相关线索:陈毅同志的报告,是指1954年4月至6月间,时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的陈毅主持召开的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于6月7日的总结发言和会后他于6月21日向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提出关于召开山东省党员代表会议,改山东分局为山东省委和建议对向明问题的处理意见,与文稿中括注的内容完全吻合。然后,又据此从档案中查找到195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陈毅同志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筹备会上的总结发言》的档案件,此件的封面上有一批注:“明(廿三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时,有关资料还表明: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舒同,这时中央决定调其到山东分局主持工作,也与文稿中宜请他到会相关联,亦可为佐证。因此这就可以确定:这一文稿是写于1954年而不是1955年,并在编排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新增编入公开版的文稿中,也有与上述内部版文稿相同的问题。如《关于三个文件的传阅讨论事给刘少奇的信》,这一文稿的落款时间也没有年代,只有日期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文稿中说:“三个文件都看了,均同意。我这两天不大舒服,今天不进城了。请你邀集朱、陈、邓、习、富春、饶、安、乔木、尚昆诸同志将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一次。”初编时,按照档案标注的年代编入1951年。但在进一步的研读中,发现文稿中所述的人物、史实,在1951年的这一时间内均未找到相关点,却有两点存疑。其一,是邀集对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的诸人中,没有周恩来。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并为政务院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在这样范围内传阅和讨论文件,他是不应缺席的。同时查明,这时他在京并无重要外事活动,没有理由不出席会议。而邀集传阅并讨论文件的邓小平、习仲勋、饶漱石,当时分别在西南、西北、华东中央局工作,且均不在京。其二,文稿中提到的传阅并讨论的三个文件也难以查明。因此,初步判定这一文稿的年代不是1951年。那么,这一文稿应为何年呢?随着对文稿的系统编辑和研读,得到了这一文稿的年代答案:应为1953年,而不是1951年。其根据是1953年10月下旬,有两篇文稿与此件提及的内容相关:一篇是1953年10月23日的《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在本篇给杨尚昆的批语中说:“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这一批语与《关于三个文件的传阅讨论事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及的几项内容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一是“三个文件”,可以看出是指毛泽东审阅的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1953年10月22日分别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二是批语中提到的“进城”,与信中提到的“不进城”,表明此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场所相同,是往返于城内外即中南海与玉泉山间;三是文中均将饶漱石、安子文并提,说明这是在他们分别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之时。而1951年饶漱石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53年4月才正式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这就与文稿中将此二人并提的史实吻合了。
另一篇是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对周恩来22日一份报告的批示。周恩来在关于黄华将赴板门店参加政治会议会谈及自己因病需离京易地休养的报告中说到:“今晚复经医生们会诊,认为我可以离院南下休养两星期,从明(二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四日止。”“故我拟预二十四日离京赴沪,易地休养十天。”毛泽东批示:“均同意。到沪(或杭),以静养为宜。”这一文稿的内容告诉我们:信中邀集对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的诸人中没有周恩来,是他因病离京易地休养去了。而这时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邀集他们参与讨论就是很自然的事。上述人物、史实的多项对应可以得出判定,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年代是1953年而不是1951年。
二、从信封或信笺上的信息质证
在文稿的编辑中,编辑者看到书信类文稿落款没有年代的最多。但书信档案中却有一些留下了信封,有的还是贴有邮票的实寄封;一些书信的信笺是印有机构名称笺头的。其中的信息也是对文稿考订的重要依据。
文稿中有多封书信的年代订正,就是来源于信封上的信息。如《关于休养事给马叙伦的信》,这封信后落款只有日期四月十九日,原档案标注年代为1950年。但这封书信档案中附有毛泽东书写的信封:“高等教育部马部长”。信封上“高等教育部”这一信息使编辑者对这封书信的年代存疑。经查,国家高等教育部成立于1952年11月,马叙伦为首任部长,任职至1954年9月。将这封信定为1950年显然与史实不符,按其任职期推算当为1953年之后。那么这封书信写于何年呢?编辑者进一步查阅马叙伦的相关资料,找到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长期保管和研究毛泽东手稿的专家齐得平的考证文章,他在《毛泽东致马叙伦两封书信年份考》一文中,就查证了这封信的年份为1954年,并附有马叙伦这封给毛泽东的信的手迹照片,信后落款为“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就是毛泽东给马叙伦的这封信中所说的:“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从而使这封信的年份得以确认。虽然在文稿的编辑中,开始因资料收集不全而走了一些弯路,但这一考订思路是可取的。
特别是一封《给宋庆龄的信》,这封信的落款署时,毛泽东明确写有年月日,即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文稿内部版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均按此时间编入了这封书信。在对文稿档案的核校中,编辑者发现这是一封寄往上海的实寄封,且信封保存完整。经仔细辨认信封上的信息,对这封信的年代产生了疑问:一是信封上所贴邮票是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所发行的“纪37”号票,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可知此枚面值8分的邮票发行日期为1956年11月10日。如果这封信的时间为1956年1月,则不可能贴有此枚邮票;二是辨认信封上的邮戳,可见邮寄日戳的日期为:57.1.27,标明这封信发出的年月日。为了订正这封书信的确切年代,又根据信中提及的内容,查阅了宋庆龄此间的相关活动。据《人民日报》记载: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间,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先后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访问,2月5日从昆明飞抵北京。毛泽东在信中说“贺年片早已收到”,这与宋庆龄当时的活动不吻合,在此过程中她给毛泽东发送贺年片的可能性不大。而毛泽东对宋庆龄参加这样重要的国务活动应是知晓的,不会在她不在上海时将信发往那里。此外,毛泽东在信中说:“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对于此事,据当时陪同江青去苏联治病的李公朴之女张国男回忆,江青这次去苏联治病是1956年5月出发的,故1956年1月此事当未发生。因此,可以确认《给宋庆龄的信》年代有误。
但文稿内部版编入毛泽东写有这一年月日的书信共3封,除给宋庆龄的这封外,还有给他的老师黄宗溍、朋友许志行的信。那么其余两封的年代是否也有误呢?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稿档案,我们进一步确定:这3封写有同一年月日的书信,年代均应为1957年,写为1956年应为毛泽东的笔误。其中《给黄宗溍的信》已有人指误,当时在首钢经办过此信的当事人徐炳忠以《毛泽东尊师重道的一段往事》为题,在《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对这封信的年份作了说明:他经办这封信和黄宗溍亲属提供的相关材料证明,这封信是写于1957年。另一封《给许志行的信》,据许志行本人回忆,毛泽东给他的这封复信年代为1957年。按信中所约,1957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许志行,并写信给韶山乡,请他们接待前往韶山的许志行。毛泽东《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时间与信中所说“暑假可去韶山”相一致,也是对这封信写于1957年的佐证。
毛泽东的这3封信所署年份为什么会出现笔误?编辑者认为可能是因岁末年初,对新旧历法记忆混叠所致。因1956年(农历丙申年)十二月与公元1957年1月的日期同一,容易造成混淆。根据上述考订和史实,文稿公开版将这3封书信编在1957年,并对毛泽东所写年份加注说明。
信笺上印有机构名称的笺头也是考订文稿的重要参考。从文稿档案中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使用的公用信笺的笺头,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除最后一种笺头使用时间跨度较长外,其余分别反映了时间的先后。其中一封《给仇鳌的信》,书信手稿中落款署时只有“十月七日”,没有年份。但中央档案馆编的《毛泽东手书选集》《毛泽东书法选》均判定为1958年。这一年份判定准确吗?信笺的笺头上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字样使编辑者对这封信的年代存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再设立此机构。信笺上的这一信息反映出,这封信至迟也应是写于1954年9月之前,1958年是不可能使用带有这种字样的信笺的。根据书信中所述,查找九月十八日仇鳌来信未果;而信中还提到“先生安居甚慰”,这就提供了另一线索。在查阅仇鳌孙女仇君好所著《诗剑弦歌——仇鳌传》中得知:仇鳌是1950年秋迁居东直门内北小街草厂胡同14号的,毛泽东1951年10月7日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即有“谨祝新寓吉胜”之语。如是1958年,事隔多年后当不会再提安居之事。此传记还明确记述:毛泽东这封给仇鳌的信时间是1952年10月7日,次日仇鳌即收到毛主席红笺头的回信。据此,编辑者认为这个年份是可采信的,即将这封信订正为1952年编入文稿公开版。
三、从手迹书体异同上辨正
本书中编入的文稿篇末都附有刊印说明。根据手稿刊印的是指毛泽东用毛笔或硬笔书写的手稿。在编辑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毛泽东手迹书体,在不同年代是有明显不同的,这也是考订文稿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比如,文稿内部版编入的一篇《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这篇给陆定一的批语落款署时为“一月五日夜”,没有年份。内部版在编辑时为了解批语中所说的“国际问题文章”和文稿的年代,曾送请陆定一认定过。陆定一在1982年6月12日批注:“两种可能”:“1957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艾森豪威尔主义》;1966年1月7日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约翰逊政府的大阴谋》,请查一查1966年1月5日夜毛主席是否在北京。如在,那就定为这篇文章。”后内部版确定为前一篇。在核对文稿档案的手迹时,感到这一批语的手迹书体与上述年代明显不符。由于文件档案存放年代错位,当时编者和陆定一可能均未注意到这一点。编辑者根据对手迹书体的辨别,进一步查找到:这是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间,毛泽东审阅陆定一撰写的署名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过程中,写的批语之一。并经与此前12月15日、12月31日两件批语手迹比对,书体完全一致。因此确定这一批语是写于1947年1月5日,不在本书选收范围,故从文稿中撤出。
再有文稿内部版中1953年《为华北烈士陵园题词》和1957年《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也是通过手迹书体比对后加以订正的。在编辑中,发现两篇题词文字完全相同,即:“为国牺牲,永垂不朽”,这使编辑者对此产生了疑问。因毛泽东没有在不同时间里题写过文字完全相同的题词。然后再将两幅题词手迹书体加以比对,书体竟完全一致。如果前一幅是首次题写,那么时隔多年的后一幅就只能是复制品。通过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了两幅题词的情况。“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应是1953年为华北烈士陵园题写。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的说法,是根据195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但浙江省洞头县文物保护所的柯旭东在《大众文艺》2010年第9期发表的《胜利岙争夺战遗址及意义思考》一文,介绍“洞头革命烈士墓”的情况时说:“纪念塔高11.6米,正面直书仿毛泽东书体‘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当地文物部门的说法应是有根据的,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不准确的。据此,将1957年《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从文稿中撤出。
还有文稿内部版编入的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和1950年12月2日《给黄念田的信》,编辑者在核校两封书信的手稿时,比对两信手迹的书体完全相同,落款署时均为“十二月二日”,但都没有年份。对此,可以认为其中的一封年份肯定有错。到底是1949年还是1950年?或两信的年份均有误?首先从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入手,查找信中所说“十一月四日”来信。经查公开出版的柳亚子文集、选集,均无所获。但编辑者仍不放弃,最后终于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了柳亚子的这封信。他在1950年11月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十月二十九日离沪,初闻弼时同志噩耗,此为四八烈士后中华民族又一大损失,思之泪下。三十日在京沪车中,有一唁函,并附拙诗四首,未知收到否?信中还说:去岁主席与朱总司令为弟题字的纪念册,六月二十八日夜在颐和园画舫中面交周总理,请其续题,乃事隔年余,消息杳然。主席为敬老崇文起见,有文史研究馆之设,感佩无任。但时隔一年,尚未开馆。弟愿主席加以督促。信中所述,与毛泽东复信中的内容完全吻合。据此,即可确认毛泽东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年份亦应为1950年,并改正编入文稿公开版。
四、从对同一文稿不同版本的内容校勘中确正
文稿内部版出版后,其中一些文稿先后被编入不同的文集公开出版。内部版文稿中的差错有的仍继续沿用,有的在公开出版时作了订正,也有的出现了新的误差。对于这类文稿,在编辑中特别注意了校勘和确正。
如《关于海军建设写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写在一页线格纸上的一段文字,上面没有年代和时间标注,但档案件将此归在了1952年11月17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等《一九五三年海军建设计划》的报告件中。据此,文稿内部版将这段文字确定为1952年11月编入。随后,1993年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只是改写了标题,将原标题改为题注,原文照录编入文集中。1998年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在编辑《毛泽东文集》过程中复核这篇文稿时,发现《当代中国海军》一书中引用了这段话,并明确指出: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所作的完整表述。为此第一编研部致函海军政治部,请他们帮助审核这段文字或提供所根据的档案资料。海军政治部很快复函告知他们复核和引用这段文字的情况。信中说:关于这段文字,有毛泽东同志手稿(现存中央档案馆),但时间不详。《当代中国海军》一书中引用的1953年12月4日这段文字,是根据周恩来1954年1月23日给萧劲光司令员的信及附件,原件在海军档案馆,并复印提供给编研部。据此,《毛泽东文集》中对这篇文稿作了订正,时间改正为1953年12月4日,并在刊印根据中注明:“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同时加写题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按照刊印根据,《毛泽东文集》中编入的这篇文稿是准确的。因此,201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据此原文照录。因为这篇文稿编入多本公开出版的文集,我们在这次文稿的编辑中,将手稿和相关档案作了进一步复核,确认这件手稿是毛泽东为在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写的一段文字,但与周恩来1954年1月23日给萧劲光的信附件中的个别文字略有不同,而档案中保存的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记录手稿,与毛泽东的这一手稿几乎一字不差。因此,编辑者将刊印说明改为“根据手稿刊印”,并按手稿对其中的文字作了相应的改正。
再如,这次新增编入的一篇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的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档案件中注明:这是毛主席在1950年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写的题词。但中央档案馆编的1984年出版的《毛泽东题词墨迹选》、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手书选集》均注明为:“为《北大周刊》题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有著作和网文中有类似说法,但时间上有注为4月20日或5月。因为题词落款未署时间,那么确切的题词日期是如何确定的?开始编辑者并未看到相关档案。在查阅有关资料中,从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从图书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找到了线索。文中说: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31周年,筹办有关史料展览,1950年4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这次纪念活动和展览题字,第二天毛泽东即写了这幅题词。为了弄清这幅题词的原委,编辑者前往北京大学档案馆,找到了这幅题词的相关档案,即:1950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写给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敬祝身体健康。”毛泽东次日即在来信上批写:“照写如另纸。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并另纸写了这幅题词。那么,为什么又有说是为《北大周刊》题写呢?于是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了《北大周刊》。原来是1950年5月4日出版的《北大周刊》“‘五四’三十一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刊登了这幅题词的手迹,而并非为《北大周刊》题写。据此,编辑者在文稿公开版中,以《北京大学举办纪念五四运动有关史料展览的题词和批语》为题,既收录了这一题词,又收录了毛泽东在来信上的批语,并加注了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来信,从而廓清了此前不同说法。
五、追根溯源,慎用订正
这次修订、增补文稿的体例规范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编辑中要保持文稿的原貌,有明显错漏之处,均采用订正处理,不得随意改动。根据这一要求,编辑者对文稿内部版中个别订正、改动不准确之处,作了恢复处理。
比如,文稿内部版1950年6月间有3篇文稿,对涉及渡江作战的起始时间曾作了订正和修改,这3篇文稿分别是:
1.《为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歼敌人数给李涛的信》(1950年6月5日)。这封信中毛泽东的手稿中有一句话:“我要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材料。”毛泽东所要的数字是为次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引用的。文稿将廿日订正为“廿〔一〕日”,并在注〔2〕中引用了毛泽东6月6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的一段被修改过的文字。
2.《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这篇书面报告,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1950年6月13日第一版,其中第二段有一句话:“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文稿将这句话改为“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人民日报》原文是四月二十日,文稿内部版改为四月二十一日。
3.《对聂荣臻军事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0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这篇军事报告稿时加写了几段文字,其中一段文字的手稿是:“若从去年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五月为止……”文稿篇三在编入这段文字时,将这段文字中的“四月二十日”改为“四月二十一日”。而公开出版的《聂荣臻军事文选》中的这段文字,就是按毛泽东修改的手稿发表的,并注明这篇报告事前经毛泽东主席审查修正。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中这一被改正的日期、《对聂荣臻军事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0年6月15日)中这一被改正的日期,后又以《目前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人民解放军必须谦虚谨慎维持良好的纪律》为题,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编者认为这一时间有误,特别在两处加注:“实际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十八时开始渡江。”这里作者原文本未错,而是编者误改了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根本点是对渡江战役的起始时间的认识有误。编者可能认为渡江战役是根据毛泽东、朱德1949年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的,想当然地认为渡江战役的起始时间就是4月21日。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这个命令,其题注就明确地表述为4月20日夜起。1949年4月2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两则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也是这样表述的:“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此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渡江战役”词条,对渡江战役的起始时间亦表述为:“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20日夜发起渡江作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渡江战役起始时间的表述也基本相同,即:“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
以上文稿内部版的修改、订正处,这次在文稿编辑中均恢复了原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公开版的修订、增补对文中使用的古汉语通假字和现在不常用的词汇如何处理,开始意见也不尽一致。在听取语言文字专家的意见后,决定不作订正或改正处理。为了使读者不致疑惑,编辑者对其中的古汉语通假字采用加注说明,如“警”通“驚”、“尝”通“常”、“景”通“影”、“指政”通“指正”等。对一些不常用词汇,如“清况”“马糊”“神旺”等,经查汉语词典有据的,均保留原貌,不作改动或订正。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微信公众号。作者系国防大学原科研部编研室研究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副主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