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饭白荣助口述,李素桢、李克俭整理。
导语:1944年,12岁的饭白荣助跟随家人一起来到当时的伪满洲。他们一度和其他日本人一样,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妄图未来能在“满洲”建设五族协和的理想国家。随着日本的战败,饭白荣助不幸成为孤儿。他经过在吉林农村的生活、儿童团的活动、人民解放军大熔炉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锤炼,渐渐认清了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而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不正视侵略历史的行为,并成为和平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
我是一个侵略过中国的战败国的孤儿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饭白荣助,1933年1月出生在日本东京,1944年读完小学五年级后,当时日本有向中国大量移民的国策潮流,父母和大姐便带我一起来到当时伪满洲国的内蒙古王爷庙定居,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郊五公里左右的农村。
当时的我和其他的日本小孩一样,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正义的,那是为了东洋和平,在“满洲”是建设五族协和的理想国家。少年的我认为,五族之中最优秀的是日本的大和民族,蔑视其他民族,瞧不起中国人。学校还把稻草扎成假人,让男孩子们用竹枪对着稻草人练习刺杀,女孩子们用两米长的竹竿进行长刀的练习。下课放学后,我们必定是玩战争的游戏,大家都梦想着参军,当日本兵。我们认为日本是神国,必胜,而“支那兵”软弱,必败,等等。但结果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苏联进攻东北的关东军。日本关东军完全不是对手,溃不成军。丢弃日本民众,逃跑了。相关职能部门,比如机关、警察、特务机关、地方行政机构,统统溃散,日本居民流离失所。因而,开拓团的人员特别混乱,没有人领导,乱成一团。青壮年的日本开拓团成员都被关东军强征入伍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了艰苦的逃难旅程。途中被苏军和当地的土匪袭击,不少人遇难身亡。一个更严重的现象是,在逃难过程中,由于长期受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我们抱着宁死不受屈辱的军国主义信念,很多人自杀或是被自己的亲人杀死。为了不当俘虏,很多父母自杀前先把孩子掐死;全家服下氰化钾自杀的很多,也有集体自杀的。现在,我有时想,幸亏我父亲在日本投降前得病死了,如果父亲当时还活着,我能不能活下来呢,是否也会像有的日本少年那样被自己的家长给杀了呢?
逃难的过程中我和母亲失散了,从此杳无音信。后来受到中国农民的救助,我和大姐在一个中国农家生活了下来。那期间我也是一个劳动力,一面种地收粮食,当地不种水田,多是高粱、谷子、苞米,一面放猪、放牛,冬天帮忙拾柴火,等等。村里的同年龄段的中国人也都干着差不多一样的活。
当时社会大变革,土地改革,斗争地主,诉苦运动,拥军爱民,组织儿童团……虽然那些翻天覆地的运动,我当时不太清楚其意义,但是对一个日本少年来讲,允许我和中国少年一样参加,没有差别和歧视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令我非常感动。因为我是一个侵略过中国的战败国的孤儿呀。我想你们大家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感激心情。
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一次,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解放军住在我家里,其中有个干部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日本人,特别是医疗单位的技术人员很多是日本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非常激动,忍不住马上就去报名参军。于是1947年的春天,我到区政府报名参军,征兵的人问我多大了,我回答说14岁,他们一听就说不行,太小,让我回去。
1948年2月开始,解放战争已经转为战略反攻,部队又开始征兵。于是我和平时一起玩耍的3个中国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当时我已经15岁了。我被分配到辽吉军区卫生部干部疗养所,所里的医生是日本人,护士大部分也是日本人。附近还有辽吉军区第三十六病院,病院中也有大量的日本医生、护士和其他的技术工作人员。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日本医生大桥的翻译、通讯员和助手,并且照顾大桥医生夫妻的日常生活。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小鬼”。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我们休养所也跟着从洮南、郑家屯、四平等地转移,直到辽沈战役胜利后,转移到锦州。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后,有一部分部队被就地整编,剩下的队伍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编入了第四野战军,跨过黄河、长江,一直打到广州、海南岛。我当时留在了辽北省军区卫生部,后更名为辽西省(现在的辽宁省)的省政府门诊部工作了。
这期间,每天早晨和晚上,在业余中学学习文化,同时学习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时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学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还有一些时事问题和理论,比如《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等等。那几年我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基础比较差,理解上相对比较困难,应该说我的进步不是很快。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当时,机关工作的人员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情绪非常高涨,大家纷纷签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不例外。省卫生部组织的卫生队需要补充人员的时候,上级意外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1951年5月,我随部队从集安渡过鸭绿江,经过江界、球场(地名),来到中部战线,在第一后勤部第二大站卫生队开始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药品、卫生器具的管理,还有跟着医生做一些看病治疗的辅助工作。当时我们单位没有一个人会说朝鲜话,有时,村落里住着的朝鲜人过来看病,沟通起来问题很大。还好居民里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些会说日语,终于通过我实现了沟通。1953年的一天,政委找到我说:七八月份有可能和美国签订停战协议,这两年国内从四野复员的日本人很多都回国了。并告诉我退役后,返回中国要继续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理论和著作,还说些注意保重身体等的安慰话语。我很感动,流下了眼泪,当时和政委紧紧握手的场景至今还在眼前浮现。不久,我跟在一起工作的富医生、张医生、于护士长、文化干事等人一一告别,到2011年已经分别近60年了。当时,我也和朝鲜居民告了别,他们在食品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还给我开了告别宴会。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朝鲜冷面。他们还赠给我亲手做的绣花领子、手帕,等等,我非常感动。
我成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
从朝鲜战场回来时,记得拿着政治部发行的通行证、还有一些钱,坐了几天的卡车,最后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4月初到达沈阳后勤部招待所。那时,上街就看到胸前挂着“回国日侨”标签的日本人,他们都穿着新衣服,两手拿着买的东西。作为一名转业军人,1956年6月,我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单位是辅助车间。1957年,参与制造的第一辆国产“红旗”牌高级轿车,赠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当时我和第一汽车厂的职工们一起敲锣打鼓,感到非常荣耀。
转业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学习,使我逐渐成长了起来。我渐渐明白了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理解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通过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对统一战线等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有了深刻的领悟。

我1958年回日本后,日语说得不怎么流利,经常不自觉地说汉语,我想回第二故乡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当时不行,两国还没恢复邦交。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刚一恢复,我就立刻回来。对我来说,就像新媳妇回娘家似的,我组织了日中友好访问团,还做了印着“回娘家”三个字的一面旗,举着那面旗回到东北,回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第二故乡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甭提心里那个高兴劲了。
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娘家”。2011年,有一次长春的报纸报道我访问参观汽车厂以及曾参加制造第一辆国产红旗牌高级轿车的事迹,报纸上刊登了我的照片。那天晚上,报社记者打来电话,说是一位老战友要来见我。
晚上8点钟左右,在报社记者的陪同下,一位高我一头左右身体健壮的老人进来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在今天的报纸上见到你啦!还记得我吗?”他的粗眉毛大眼睛把我的记忆带回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呵,您是张医生!”我俩几乎同时喊出:“58年啦!”我们分手58年了,双手紧紧地握着,好半天也不松开。最后张医生说:“你看,我带来了什么?”他从包中拿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中夹着一张黑白小照片。那是我58年前离开朝鲜战场时,送给张医生的。略微发黄的小照片背后,我的字迹“饭白”还清晰可见。报社的记者、张医生的孙女等人都围了上来,争相看我年轻时的照片。之后,我们各自介绍战场一别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张医生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被派去支援西藏、云南等地工作,晚年退休后定居长春。虽说时间可以磨灭一些记忆,但是战火硝烟中的记忆,难以忘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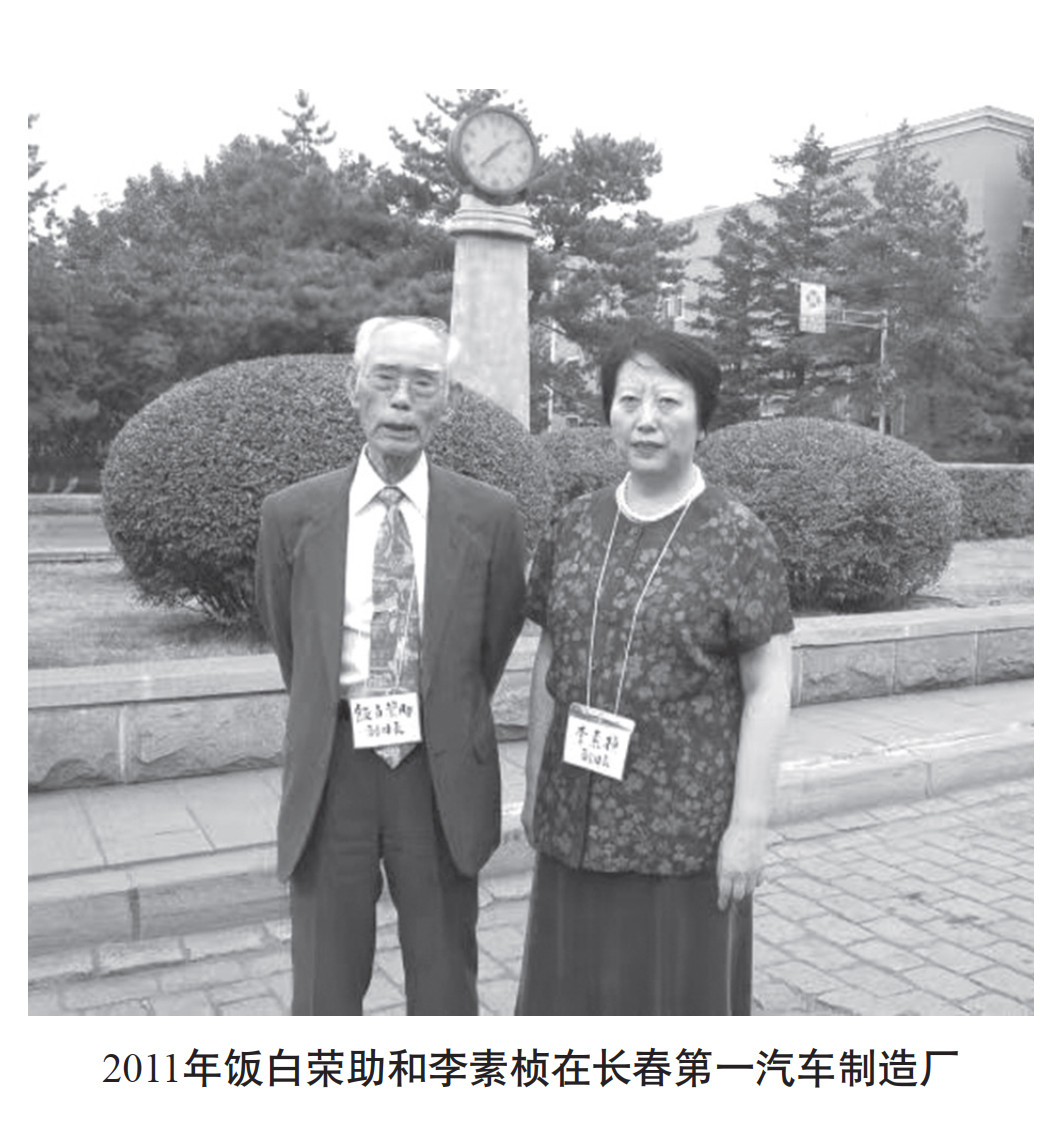
我告诉张医生回到日本后,为日中和平友好,我努力组织各项活动。几乎每年都来东北—我的第二故乡,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纪念馆”“平顶山同胞受难地”“七三一细菌部队遗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等教育基地,向日本人民宣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个人在日中友好协会任理事,常常向日本青年们讲述我的战争经历和体会。
多年来,我用历史事实说话,揭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中国的暴行,为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永不再战,贡献我的晚年。
(本文整理者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